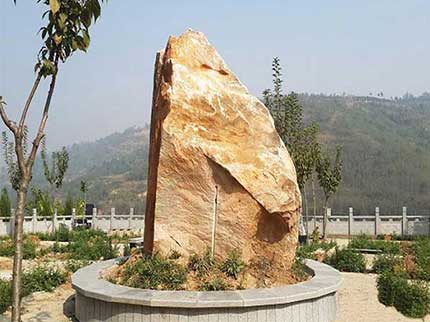南北朝時期清河張氏的喪葬習俗593-臨潼殯儀館骨灰堂
葬俗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,它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,有其獨特的文化地位。我們通常將正常的死亡稱為正寢,即*終正寢,其最重要表現形式就是死在家里,對于這種死亡方式,我們普遍認為是最為正常的,喪事按照程序辦理就行了。但是,從歷史上看,人類的流動性決定了并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“*終正寢”,譬如外出做官或者打仗,死在官員任職的地方或者死在戰場上也不在少數,這些人面臨一個問題,就是如何殯葬?
鑒于這種情況,在殯葬方面,人們大多采用了歸葬還鄉的方式,所謂葉落歸根、狐死首丘,都是這種情感的形象比喻。不僅如此,人們在《禮記·檀弓》中找到了儒家文化的理論依據:“大公封于營丘,比及五世,皆反葬于周”。君子曰:“樂,樂其所自生,禮不忘其本。古之人有言曰:‘狐死正丘首’。仁也。”《禮記》中此句話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喪葬習俗。

歸(鄉)葬,通常指死于外地,返葬于父祖之墳塋,亦稱“歸窆”。歸葬作為中國古代喪葬習俗的一種,反映了當時社會人們的死亡觀念,對家族、家鄉的重視。所謂“歸葬”者,要體現一個“歸”字,如果沒有“死于外”這一前提條件,那么就談不上“歸”。歸葬的施動者一般為死者的后代子孫,這也是他們“盡孝道”的一種體現。從一定程度上說,是否能讓死去的親人實現“歸鄉葬”,乃是展現其是否恪守孝道的直接表現。
魏晉南北朝時期,由于戰爭的原因人口流動頻繁,客死他鄉之事頻率增加 ;加之門閥士族的興盛,時人對家族門第的重視,使得歸葬之風猶盛不衰,歸鄉葬因而成為一種普遍性的葬俗。南北朝時期張姓族人張彝與張讜,用他們的實際行動,使親屬魂歸故里,盡善盡美,譜寫出了大孝的感人篇章。
張彝(-年),字慶賓,南北朝時期北魏清河東武城(今河北清河)人。其才華過人,性格張揚,為民族融合、國家穩定做出了重大貢獻。張彝雖然性情豪放不羈,但素有孝名。其父早亡,與母親相依為命,每天早晚耐心侍奉,從不懈怠。母親去世后,張彝悲痛萬分。作為一個孝子,把母親的喪葬之事辦好是義不容辭的責任。于是,張彝解除官職,扶喪歸葬武城故里。他守喪超過禮節的規定,從平城(今山西大同)到家鄉一千多里路,他完全步行,不乘坐車馬。等回到武城時,他面色憔悴不堪,形容枯槁。世人皆為他的孝道稱贊不已,乃至于當時的皇帝孝文帝知道后,也派遣使節前來吊唁與慰問。張彝排盡千難萬險,使其母“歸鄉葬”,成為一則“首孝悌”的美談。
無獨有偶,《魏書·張讜傳》中關于其歸鄉葬的記載更加波瀾曲折。
張讜,字處言,清河東武城(今河北清河)人。入魏后,他與宗族保持了十分密切的聯系,史載曰:“性開通,篤于撫恤,青齊之士,雖疏族末姻,咸相敬視”。延興四年(公元 年),張讜卒于東徐州(今江蘇邳州),其子張敬伯上奏朝廷請求葬于清河舊塋,朝廷遷延不允,最終“停柩在家積五六年”。張讜的另一個兒子張敬叔在徐州,聽聞父喪不許歸葬,甚至秘密謀劃南叛,后被徐州府衙押送京師。至京師后,他不畏強權,據理力爭,直至后來得襲父爵,出任武邑(今河北衡水)太守時,方得葬父于清河祖塋。
為什么張讜的后代寧愿與統治者據理力爭,也要讓張讜歸鄉葬?說起來還是與當時的社會風氣相關。歸葬習俗歷來受到重視,而鄉里、宗族等地緣、血緣關系,也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。關于不歸葬的后果,最典型的事例當屬《晉書·陳*傳》中的記載:西晉時陳*的母親卒于洛陽,遺令葬于洛陽。陳*遵其志,不歸葬,結果以不歸葬母被罷官,而且受到時人的貶斥。陳*遵從父母之命不歸葬,不管其內心多“孝”,不歸葬親人遺骸,從形式與內容上都背離了傳統喪葬習俗的要求,為世人所詬病,被視為大不孝。我們不知道張讜的后代是否有此一慮,至少從倫理、感情上來說,其熱愛家鄉,眷戀家鄉的傳統美德是確定無疑的。
總而言之,不管是死者生前的遺愿,還是子孫后代恪守孝道主動要求歸葬,歸葬的風俗,從來不曾消失過。歸葬,不僅便于后人祭掃,也無疑對家族起著凝聚的作用;歸葬,已然融為中國孝文化的傳統禮法。顯而易見,張氏族人張彝與張讜之子將其親屬遺體歸葬故里,是當時傳統士族重視歸葬風俗極其普遍的做法,更是恪守中國傳統禮法的必然選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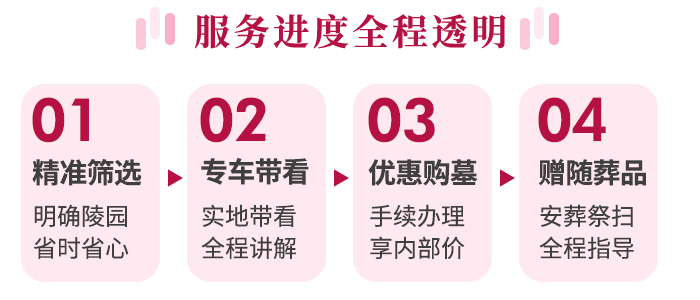
文章來源:網絡 | 更新日期:2023-05-29 18:14